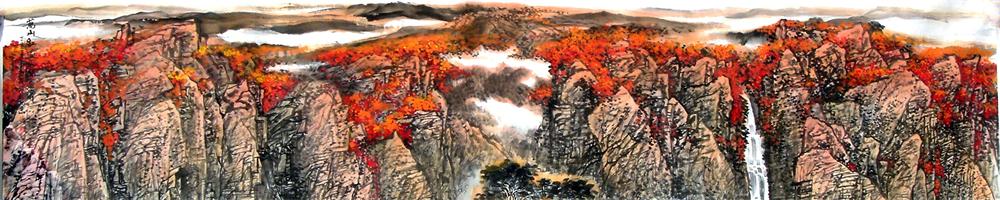

| 近距离地触摸印度 ----丹青之旅之三十六 |
 |
文 谭翃晶 从小到大,印度总是透过各种媒体在视野里晃动,印度特色的歌舞电影,奇异的香料,不眠不休的瑜珈,婀娜多姿、野性不羁的印度美女……从世界地图上看,她是一个被孟加拉湾、阿拉伯湾和印度洋环抱的亚洲半岛,在历史书上她有很崇高的地位,是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2007年1月7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旅游联谊中心承办,中国美术名家印度第八采风团在北京正式启程。全团17人,团长由尼玛泽仁担任。成员有杨力舟、王迎春、吴长江(名单全打)此次我客串领队,所以还没有出发已经感到压力。飞机经上海转机飞行大约8个小时在晚上9点多钟(当地时间)到达德里。下飞机后出关、安检折腾了近三个小时,到达酒店已是当地时间23点钟,北京时间大概凌晨2、3点钟,我们已经疲惫之极,一觉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快到9点钟了,才见到我们的印度导游哈门(中国名字叫宝玉)。他一见面就一个劲地“Sorry! Sorry!”他说由于星期一早晨德里非常的塞车他来晚了。从外形上看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棕色的皮肤,大大的眼睛,黑而长的睫毛像雨蓬,挺拔的鼻梁下是一脸黑亮的落腮胡子。猛一看有三十多岁,后来才知道他只有24岁。大家都说:“宝玉你刮掉胡子会更年轻、更好看。”他摇着手乱晃:“No! No! No!我们锡克教的男人终生是不能刮胡子的。”我们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在机场见到那么多大胡子的老人家。他的中文说得不太流畅。听他自己讲他的中文是在德里大学用汉语拼音花一年时间速成的,只会讲口语,不识汉字。但是他有非常灿烂的笑容和异常聪颖的记忆,这一点为他语言的不足弥补了许多。 车子刚一拐上德里的街头,令人诧异的异国风情就排山倒海地扑了上来。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的首都像德里这么热闹、这么拥挤。大车、小车、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马车、牛、狗、羊、猪、大象、骆驼以及身着各色艳丽服装的男人女人混杂在一起,合着印度音乐的跳动和喇叭的轰鸣,裹着奇异的印度香料的味道和扬起的尘土,全方位地将我们包围。街上也有红绿灯,但行人显然没有把红灯放在眼里,车也不自觉,更别说动物了。我们的司机似乎司空见惯、处变不惊,居然能在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看得我们惊心动魄,心跳不已。尼玛泽仁和房新泉坐在车子前面又会开车,直惊呼“受不了,受不了”。宝玉开心地摇着手:“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印度的司机都是顶尖的。”车子冲过人墙后在印度门、总统府和国会大楼前打转,之后参观甘地陵和胡马雍陵。甘地陵是印度前总统甘地遇刺后火化的地方,他在印度人民心中有国父般的地位。胡马雍陵是印度最著名的莫卧儿王朝开国君主巴布尔之子、第二代帝王胡马雍的陵墓。之后,我们又回到车上,继续穿行在熙熙攘攘的公路上。向斋浦尔驶去,二百多公里的路程用了将近6个小时!每次将去一个地方我们都会问宝玉需要多长时间,他总是笑嘻嘻地回答:“大约XX时间左右。”后来几天我们才知道这个“左右”的厉害。在印度,汽车、火车,包括飞机晚点是很常见的事,左一左可能提前一个钟头,右一右可能就要推迟一个小时或更多。到最后杨力舟无奈地笑道:“是不是还要五分钟左----右。”逗得全车的人都笑。 斋浦尔是印度北部一个美丽的城市。城市四周环以7座城门,其中建筑布局严谨,街道纵横交错,宫殿和一些古建筑虽然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但其雄伟的身姿依然可见。粉红色的基调据说是三百年前为欢迎当时还是威尔士王子的爱德华七世造访而装饰的。在印度的色彩语言里,粉红色代表着“好客欢迎”的意思。一大早,我们乘坐一种吉普车(类似我们北京郊区的摩的),一路磕磕碰碰向琥珀城堡驶去。在路上什么都能看到,除了非常多的人和车以外,还能看到许多脑门上画着彩色图案的大象,驾着木车的骆驼,四处觅食的猪、狗、羊、牛。尤其是牛,早听说印度的“牛”是神牛,是全世界最“牛”的牛。此言果然不假,它要是想趴在马路中间,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都要小心绕行。我相信全世界的牛做梦都想到这里投胎!街道两旁也很热闹,炫酷的印度音乐,不时从街边的商铺里传来,制衣的、修鞋的、雕刻的、染坊、花店,琳琳总总的商铺组成一个个粉红色的街道,店铺的屋顶上还有一些神态悠然的猴子、松鼠、各种毛色的小鸟,甚至孔雀,四处溜达……整个斋浦尔街头就像一个自由的动物园,奇就奇在所有的动物都能安步当车,看到喧闹的人群和听到尖叫的喇叭,根本不会鸡飞狗跳,大家都说印度更像是一个动物的天堂,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琥珀宫,是16世纪当地藩王的宫殿,因其墙壁上镶满镜子般的几何装饰,又称为镜宫。刚一下车,天上一群黑压压的东西忽忽啦啦向我们飞来,吓了我们一跳。定睛一看是一大群鸽子。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鸽子,他们飞到人们的手心里来啄食,一副想当然的样子。地下是密密麻麻的鸽子,头顶上是古拙凝重的古堡,周围是一些穿着远古时代同样服饰的印度人,我的感觉仿佛一头扎进了远古岁世的长廊里,意识有些恍惚……这就是那个印度吗?那个色彩艳丽、历史复杂、拥有不可一世的孔雀王朝和月亮王朝的文明古国吗?凝视着风情无限的古堡,心中不免会生出无限的悲怆和落寞。 下午,我们来到粉红城的中心,那里有一座非常华丽的“风之宫殿”。在太阳的光线下,城堡闪烁着魔力般粉红色的光芒,注视着路边眼镜蛇在弄蛇人的魔笛中欢乐起舞。密密麻麻的小档口在城堡周围组成庞杂的集市,华丽和混乱就这样魔幻般地相融在了一起。王迎春、刘素珍、李忠祥夫人张莲芝和我,我们四个人手牵手地过马路,还差一点迷失在这种百样颜色交织的人流里。到了印度,感觉就像到了人的森林、人的海洋,处处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再加上到处都能遇到乞讨的儿童,只要看见有游客过来,就蜜蜂一样地围过来,“美元”“卢比”“巧克力”“糖”“钢笔”什么都要。一开始大家都往外掏,到后来都有点吃不消了。在印度的街头行走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个人都有被团团围住的经历,大家说的最多又最熟练的一个英文单词就是“No! No! No!”  回到车上,杨力舟一边摇手一边微笑:“市场繁荣,秩序混乱。”全车人笑。一向不爱言语的吴长江也忍不住感慨道:“太乱了,简直不敢过马路。”笑咪咪的尼玛泽仁接着说:“我的感觉是两头,一头是惊讶,一头是惊喜。惊讶现代如此脏乱,惊喜古代建筑如此精美。”大家都十分认同。爱开玩笑的郭正英问房新泉:“给你10个印度美女让你到这里当国王干不干”房新泉坚定的摇头。“不干!”“20个?”“50个也不干。这么个乱法简直无从下手。”逗的一车人乱笑。宝玉说;“以前有人总结说;“印度是一个脏乱差的美丽国家。”大家一齐伸出拇指:“总结的到位!”当天晚上住在斋浦尔,晚上吃的是印度餐,大部分是咖喱饭。随团的翻译宝玉一般到酒店后就不陪我们了,剩下我们自己人开始胡乱点餐。全团英语会两下的包括刘秉江、吴长江、谢东鸣简单的问话可以应付,最过硬的当属李忠翔的夫人李莲芝。大家围在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听大家讲故事,刘秉江先讲了一个他的天津朋友出国购物的故事:“一个天津朋友到国外想买东西,突然记不清,‘How much’(多少钱)的发音了。他先指着东西讲‘吗好吃?’人家不理他,他又说:‘吃吗好?’人家还不理他,他最后急了拉长声音说:‘好吃吗?’”逗的大家把饭差点喷出来。杨力舟接着讲了个更好笑的,他说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年去前苏联,不懂俄语又不带翻译在莫斯科一家高档的餐厅点餐,服务员把菜谱恭敬的递给他,他翻开一页,指着其中一行。服务员微笑的退下去,一会钢琴声响起来,弹了很久也不见饭上来,他又把服务员叫来,指着刚才那几行,用手势问他,服务员指了指钢琴给他作了个‘OK’的手式,他这才知道刚才点的是音乐。他做了几个吃饭的手势,服务员又把菜谱拿过来,他不敢点了,想起出国前有人对他说俄式的酸黄瓜非常好吃,他就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瘪的竖起来的酸黄瓜,为了表示腌过的还在底下画了两滴水,服务员是个女的,看完后耸了耸肩笑笑,把他领到了男厕所。”他刚讲完,大家就笑翻了。李运江和郝邦义笑的差一点差了气,宋鸣一边笑一边伸大拇指。王琦说这个故事越想越好笑。“酸黄瓜”的故事让大家笑到爱庙。 1月11号我们到达阿格拉去参观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泰姬陵,门口的守卫十分严格,分男女游客,全身都要被摸一遍,这种做法多少让慕名而来的人们感到不舒服,但是没办法。只好入乡随俗,刚从拥挤狭窄乱哄哄的街道穿过,突然看到这个极尽奢华的美丽建筑,就象晴天做了一个梦,有点走错时空的荒唐感觉。尼玛泽仁说:“噢。又一个惊喜,就算搜身也值了。”郝邦义在一旁调侃的说:“等明儿个印度人要上我们的长城,也狠狠的摸他几下。”大家又笑。  泰姬陵的入口是一个气势宏伟的红色沙岩门,然后是一个波斯式样的花园,花园的四周用红色的墙体做拱门,中间是白色大理石垒砌双球形式样的泰姬陵。泰姬陵高74.21米,头顶兰色白云,脚踏碧水绿树,在耀眼的阳光映衬下,更加的玲珑剃剔透,妩媚迷人。作为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它不但宏观壮美,近观同样美仑美奂。墙壁、门扉、窗棂都雕满了精美的花纹,大理石壁上镶嵌着红、黄、兰、绿各色宝石,美的使人几乎挪不动脚步。除此之外泰姬陵最为人称道的恐怕是这个建筑背后所包含着的一个哀怨缠绵的爱情故事。 沙迦罕是莫卧尔王朝第五代国王,年青的时候,他在一个集市上与娇艳美丽、才华出众的姑娘穆塔芝·玛哈相遇,之后他们相爱、结婚。王妃一直伴随国王左右,并随国王出征。在一次远征中,因为分娩第14位王子而死去,时年39岁。悲痛欲绝的国王据说一夜白头,之后倾举国之力,用22年时间修建了这座寄托着他无限的相思的爱情纪念碑。国王本来还想在亚穆纳河对岸在为自己造一个一模一样黑色的陵墓,中间有一半白一半黑的拱桥相连,谁知泰姬陵刚刚建完,其子就篡位,他被囚禁在离泰姬陵不远的阿格拉堡。此后整整8年,每天他只能凄凉的遥望着远处河水里泰姬陵的倒影,忧郁而死。 听完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我再回看泰姬陵,觉得她就象一位形单影只的绝代佳人,在亚穆纳河边痴痴的企盼着爱侣的归来。现代人已经很少有这种难能可贵的感情了,人们都忙着自爱,只怕自己会付出多一点,所以痴情的沙迦罕越显的弥足珍贵。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泰姬陵,除了观赏建筑以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真实的触摸一下人人拼命追求,又很难求到的神圣爱情。 下午我们去参观红堡。莫卧尔王朝始建于公元1526年,是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之一。第一位是巴布尔,第三位是他的孙子阿克巴。阿克巴14岁登基,创建了印度史上著名的孔雀王朝,红堡就是他在位建的。他的儿子沙迦罕继承了王位后,使莫卧儿王朝的建筑达到了鼎胜时期。红堡是莫卧儿王朝历代帝王的王宫,整个建筑周遭都是用砖红色的沙岩建成的,城墙的第一层保卫是可以推动的大石头,第二层是蓄满护城河的鳄鱼,第三层是狮子,可谓固若金汤。但是那又能怎样呢?时光流到现在,城堡的主人都逝去了,只见乌鸦乱飞,松鼠乱窜,成群的猴子在城上成了霸王。我刚拿出来糖果一群猴子就围了上来,伸出小爪一个一个的要。郭正英的夫人蒋宛真看着好玩,也过来喂食,她想平均分配,把食物藏了一点,没想到小猴子火了,扑上来就抢。房新泉更惨,本想照张像,结果被猴子隔着衣服咬了一口,大概嫌他没给吃的。大家吓的逃开,直喊:“惹不起!惹不起!”宛真气得直嚷:“都是人们把它们惯坏了。”大家一齐笑。印度的神太多了,除了创造神、保护神和破坏神这三大神外,还有许许多多诸如大象神、猴子神、牛神、孔雀神……等等的动物神。人们哪个也惹不起,这个国度匪夷所思的文明太多了,复古元素与现代元素乱七八糟的胶合在一起,经常惊的你张口结舌。 第七天我们去参观了位于克久拉霍的爱庙,这种感觉几乎达到了顶峰。克久拉霍寺庙群,先后建于公元950-1050年,原寺总数85座。由于战乱的损毁现存20座,整个建筑用土黄色的沙岩建成。数百幅表现性爱的浮雕是根据8世纪《爱经》的内容雕刻而成。印度教里有一个支脉叫怛特罗,怛特罗教义直接把性本身当作一种宗教仪式,通过一系列各种形式的交合,使男女变成一对男女神。这个过程和仪式并非取乐,而是借助性来达到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获取人生快乐。他们这种惊世骇俗的想法,通过精致入微的雕刻堂而皇之的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更别有一种卓尔不群的震撼力,一个民族能把性爱表现的如此虔诚?如此理想化,如此灿烂辉煌。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有这样鲜活的文化作背景,难怪印度人民的性格乐观、快活、富于激情、能歌擅舞,真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甚忧,回也不改其乐。”  我们在爱庙与早我们几日先去的中国美术名家印度采风第七团汇合。七团由王京宁领队,相熟的有王有政、马西光、狄少英几人,其他的人都是初次见面。我们一块去爱庙,大家在那著名的84式雕刻下面笑得前仰后合。宝玉操着言不达意的汉语给大家讲解。郭正英慢悠悠地说:“这个你不用讲大家也明白。”不知谁在后面坏坏地笑:“这时候可不能出现放酸黄瓜。”逗得杨力舟哈哈地大笑。宝玉也忍不住地笑。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汉语更加的言不达意。他越讲大家越觉得好笑,他说:“这个女士腿上有蝎子,就是要发热了,然后脱衣服。”一会他又说“这个男士要发热了,脱衣服。”听了半天大家有点明白了。七团的狄少英告诉他:“那叫发痒了。”他学得非常快,下一个雕塑他马上说:“这个男士要发痒了。”大家笑成一片。各种肤色的游客在雕刻前都笑成一片,黑皮肤的、黄皮肤的、白皮肤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全都无忌讳地笑。尼玛泽仁说:“我的相机已经拍得发热了。”有人马上敏感地追问:“谁发热了?”他笑嘻嘻地说:“相机两块电池都没电了,相机发热了。”郝邦义笑:“相机可以发热,人可不行。”不知谁又喊:“老郭可以。”大家又笑个不停。在这里我才知道“蜜月”的来历。它源于一个印度神在订婚的时候,月亮女神送给他们一坛蜂蜜。 下午我们放弃了去老虎园,一块和七团的朋友去乡下采风。乡下的环境乱,条件更加的脏乱和差,许许多多的人只住在一个茅草屋里,男士们原想去拍摄那些体态婀娜,顶着水罐的纯朴美丽的乡村姑娘,结果与想象出入太大。女人有很多,大部分都衣衫不洁,又黑、又瘦,年纪轻轻的已有一大堆孩子。这里的妇女可没有泰姬那般的宠遇,重男轻女的现象在印度十分严重,成婚的时候还要向男方提供嫁妆。嫁妆不丰的,结婚后还会倍受虐待。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散尽了身上多余的零食和日用品,仍然杯水车薪,不可想象七团的同伴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呆九天,真是需要一些勇气。 第八天,我们告别了七团的同伴,告别了克久拉霍,乘飞机赶往印度的古老圣地——瓦拉纳西。下飞机后我们先去参观佛教圣地鹿野苑。穿过拥挤的人流,鹿野苑树影婆娑的绿地在夕阳的辉映下古雅悠远。大片大片的古塔遗迹斑斑,因为十分空旷,让人倍感随意和宽松,忽然有一种畅然释怀的感觉。释加牟尼原来是一位尼泊尔王子,29岁时他抛下娇妻幼子在菩提树下坐化。鹿野苑中的答枚克佛塔是他得道再生后第一次为五位弟子讲经转法轮的地方。那时候佛教在印度很辉煌,公元九世纪后,佛教在印度失利于印度教,从而不断衰落,但是佛教经唐三藏之手在中国、日本,及至东南亚却发扬光大。尼玛泽仁是我们团唯一的一位藏族艺术家,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感召下,我们全团也都跟着他一样合掌打坐,在园子里徘徊了很久。他手上的念珠在园子的每个地方都触摸了一下,我虽然不明道理,但看得出他非常的开心。 我们就这样一边观景,一边画画,走一路,买一路,笑一路,到也十分有趣。遇到好的景色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十几台照相机、摄像机,经常照到没电。照的最多的当数李忠翔和李运江。走到最后连宝玉都要嘱咐李忠翔夫人:“看看你的先生回来没有。”还有写生、沿途的景点、村庄、车站、候机厅都能激起我们的创作灵感,只要有一点时间,就会有人拿着速写本画画。杨力舟、王迎春、尼玛泽仁、吴长江、刘秉江、李忠翔、宋鸣这几位年龄较长的老师十分勤奋,而且画得都十分传神,任何平凡的景物,那怕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经过他们的笔就立刻化腐朽为神奇,多姿多彩,宝光灿烂。因为绘画使我们沿途与一些完全不相识的外国人成为朋友,有印度的、欧洲的、韩国的、日本的等等,看到有人把他们画得惟妙惟肖,他们会开心地大笑,举起大拇指:“Good!Good!”有的跑过来要求与画家照相,有的想买走自己的画像,还有的凑过来要看我们的“画画机”(速写本),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艺术使人们超越了语言的障碍,心灵的贴近油然而生。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就是购物。印度的宾馆不象我们国内,只有一个简单提供日用品的柜台,那的每个宾馆都会附属许多商店,所以晚饭之后就是大家购物的时间。因为李忠翔夫人英语比较过硬,所以大家都愿意拉着她去砍价,最难得她是有求必应。一般是先问价格,商贩先出一个,我们“No! No! No!”之后,再出一个,通常是拦腰价或更低,商贩肯定是吃惊的表情,接着他两手乱晃,你坚持,他又下一点,你又摇头……到最后,也不知道在印度算不算便宜,折成人民币觉得还可以,就成交了。经过几天的较量大家一致人为,最不会砍价出手又大方的当数刘秉江、房新泉、王岐讨价还价还没轮完两圈,他们已经掏钱了,逗得大家直乐。最会买东西的当数郭政英的夫人蒋宛真,眼光最独到的是尼玛泽仁。其实出国购物贵与便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买个开心,只要这个东西百分之百是印度的东西,自己又喜欢,这就“OK”啦。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恒河。恒河源自喜玛拉雅山,在瓦拉那西这个地方二支水脉汇合,成为印度的母亲河,而瓦拉那西则成为印度的宗教中心,它被称为“永恒的城市”。印度教徒认为,每年1月份的第3周如果人们能迎着日出在恒河里沐浴,就会消灾去病,死后升入天堂。当然一年中的每个日子都能沐浴,但这个时间是最灵的。为了一睹晨浴的神圣,我们清晨六点钟就朝恒河出发了。经过沿途的房子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贫富悬殊非常厉害的城市。富人的别墅里种满了芒果,干净而漂亮。穷人居住的地方简陋而脏乱。通向恒河的小巷里到处是尘土和粪便,刺鼻的烟味和骚味令人不能呼吸,街的两旁躺着还在熟睡的人们,有的蜷缩在人力车上;有的蜷缩在简陋的货架上;有的干脆蜷缩在地下的蓬布上。在微弱的天色中穿过这样的街道,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走到河边,大家登上先订好的小木船,船夫把船撑向河中央---圣浴的场面太壮观了!恒河两岸有一个圣地石阶码头。在这里成千上万各个阶层的人从印度各地赶来,沐浴者络绎不绝,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这里你会发现印度人对色彩的迷恋近似夸张,整个河岸就如一个由人组成的大花园,什么颜色都有,花花绿绿,色彩斑斓。还有虔诚,清晨的河水是很冰凉的,我们穿着毛衣还冻得瑟瑟发抖,他们大多脱去外衣,男人只穿内裤,也有全裸的,妇女穿着纱丽直接下水,身体侵入水中,才脱衣服。沐浴完,一边上岸,一边再把纱丽缠回去。整个恒河两岸庙宇繁复,人声鼎沸,人山人海,川流不息。所有的人都一样,贵族、百姓、乞丐,恒河将一切等级差异在这里抹平,冰凉的圣水荡涤着每一个沐浴者的心灵。我看着东岸冉冉升起的旭日渐渐照亮恒河,照亮沐浴者,再照亮岸边的火葬台,似乎看到了一个无始无终的轮回。做人是要讲运气的,一个人最渴望的东西,往往就是他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大家虽然都冻得发抖,但又都不愿离开。刘秉江说:“眼都看花了,这么多人,这么多颜色。”尼玛泽仁说:“相机又发热了。”宋鸣也一个劲的直嚷:“眼花,眼花。”还有的在说:“眼晕。”从来没见过这么奇异迷离的人海,这么原始天然的混乱。在这条颤动的生命之河旁边,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了强烈的撞击。我相信过不了多久,这些喧嚣繁忙、零乱一片的场景,就会在他们的作品中升华。 2007年1月16日我们结束了旅程,从德里机场登机返回北京。听着机舱内印度释他音乐如泣如诉的鼓点,看着旋窗外渐渐隐去的灯火,我衷心地祝愿瓦拉那西——那条主宰着印度人民生死的恒河,赶快美丽干净起来,衷心祝愿广大的印度人民赶快文明富裕起来,衷心的祝愿那些饥饿的妇女儿童赶快丰富、漂亮起来…… 2007年1月20日于北京 |
版权所有:国粹艺术网 ,是一家全国汇集传统文化艺术类信息的专业网站, 除此之外,还提供电视台录制、新闻报道、文艺评论、视频拍摄、展览发布、演出资讯、艺术品在线交易等内容,通过不断的发展,国粹艺术网已成为业内瞩目的焦点。